自漢太祖劉邦打敗西楚霸王項羽後,登基定都於洛陽,而非秦始皇贏政的咸陽都城,後遷至長安,此後,帶動長安城數十年繁華盛景。
其中,又以長安城的重心、劉邦所居住的皇城宮殿─長樂宮,集所有漢朝當代文化、政治、藝術、歷史與經濟於一身,令後世百姓讚嘆不已。
時至今日,距漢太祖劉邦帝崩已近十五載,距二世祖漢惠帝劉盈因病而崩亦有八年,爾後的前後兩任少帝皆是太皇太后呂雉的掌中傀儡。
長樂宮,是劉邦依秦朝的興樂宮改建,更名為長樂宮,待未央宮建成,稱其長樂未央,後世人意為「無窮盡的快樂」。
咚咚聲響從遠方傳來,打更的梆子重重敲了四下,有道人影自另一頭往那打更的宦者(即宦官、太監)走去。
「啊!常侍。」打更的宦者見到來人,趕緊將手上的梆子插在腰後,畢恭畢敬向對方躬身敬禮。
「丑時了嗎?」宦者行禮的對象年約三十餘,身穿青袍,衣襟與袖口鑲上深色花邊,頭戴小帽與袍色相同,這人臉色蒼白不留鬚眉;眉粗外眼角上吊;一臉肅穆,夜裡遠遠看去倒有幾分鬼樣。
至於那打更宦者,卻生得白淨清秀,若換上女裝怕是也沒人認得出來這人竟是一男子,他穿著棗紅色短袍,下著襦褲,戴玄色小帽,完全是一副雜役裝扮,由此可以看出兩人的地位相差甚遠。
被宦者稱為常侍的秦震微微點頭算是應了對方示禮,喃喃自語回望適才走來的方向,那是一座經年累月在夜裡燈火通明的無盡奢華宮殿─永壽殿。
永壽殿位於長樂宮一隅,後有永寧殿,前有長秋殿與長信殿,而前殿、臨華殿等分散在長樂宮各處。
「寅時更找人來頂,你同伯子到我那去。」秦震未等眼前的宦者應禮便快步離開,朝永寧宮旁的一間獨院矮房走去。
秦震所居住的獨院不算大,但他卻是宮廷中少數有獨院的宦者。
說起這獨院也是有背景的,當時未央宮尚未建成,漢太祖劉邦住在長樂宮時,這獨院是賜給他的面首─籍孺所住,籍孺這閹人沒什麼本事,卻很懂得如何討劉邦歡心,最後還與劉邦同住寢宮,爾後未央宮建成,漢惠帝即位改居未央宮,政治中心轉移至未央宮,長樂宮則成為呂雉居住的宮殿。
又因未央宮建於長樂宮之西,而稱未央宮為西宮,長樂宮為東宮。
至於秦震何許人也?依據宮中較為年長宦者的說法,他是服侍籍孺的童侍,雖然長得不怎麼討喜,但辦事伶俐機靈,劉邦許多不欲人知的事都經籍孺之手轉交給秦震來辦,後來呂雉知道了,也搶著要他幫忙辦事,劉邦拗不過愛妻,最後只得讓他住在籍孺這舊院。
但籍孺私下全盤否認這個說法,反倒提了另一個說法:「這秦震實為陛下在西楚霸王項羽死後所收編而來,雖為宦者,可並未曾做過那些雜役髒事,也非單單受寵而來,莫說秦震與我同住為服侍我,其實那獨院是給他住,我只是個沾光的,總之,這秦震大有來頭,莫看年歲雖小可欺,實則有莫名震怒之威、驚魂之煞,千萬別去惹這小祖宗。」
籍孺這話一傳,倒有不少人揣測這秦震的來頭,莫不是項羽的庶子吧?只是這事無人可證實。
話說回來。
秦震穿過前庭進屋後,將手上的燭火點亮油燈後吹熄,坐在主位,雙手抱胸閉目養神。
未及一刻鐘,腳步聲自遠而近傳來,秦震揮了揮手示意眼前的兩人免禮,然後睜開佈滿血絲的雙眼瞧著來人好半晌,彷彿要將他們徹底看穿一樣。
只見這兩人微微喘息,看來是用小碎步趕來,二人站的筆直雙手垂下,望著秦震的一雙血紅眼配上嚴肅的容貌,兩人不禁背脊發冷。
適才那位打更的宦者被秦震瞧著內心發顫:「男人就該同常侍這般威武,怎麼我當初犯傻,讓自己給人淨了,如果不淨身也就能成為像常侍這樣豪氣的官兒啊!」
宦者這念頭一閃而逝,轉而對秦震那肅然的面容與腰身直挺的體型,還有平時那漠然的口吻與行事風格,不由自主臉紅心跳起來,不知為何對秦震有了異樣的情愫。
「呂雉啊呂雉,妳終究難逃天理……」秦震並未查覺到宦者的小心思,他起身負手步出門外,似是緬懷地望著即將天亮的夜空。
月亮與星辰交織的夜光悄然灑落,前庭所種植的各色花花草草在這樣的氛圍之下,更顯得瑰麗絢爛,可惜秦震沒有心思慢慢欣賞,他自言自語:「十五年了,這究竟是段漫長還是短促的時日?」
秦震在長樂宮內望著這片夜色走神,同樣夜色之下的宮外,卻是另一番景象,許多大小官吏陸陸續續進宮,而在秦震適才離開的永壽殿外,早有一群職等不低的官吏守夜。
二位小宦者不發一語,亦步亦趨跟隨秦震。
忽地,夜光遭到遮掩,一片片夜雲自遠方飄來佈滿天頂,秦震似是回神轉身,口氣嚴峻對兩人道:「要變天了!」
兩人心頭一震,互看對方一眼同聲道:「常侍,棋子已安妥。」
北宮伯子仍有些不放心:「常侍,小的看鄧通不太踏實。」
「只是個棄子,無所謂。」秦震點頭,語畢,似乎是為了安撫他們不安的情緒又開口道:「鄧通只是為了掩飾你們二人而安排,此子野心極大,遲早會惹禍上身,你們只要記住,要明哲保身就別越過鄧通這條線,我為了要令你們時時刻刻警惕而將他放上的。」
兩人聽得秦震如此用意,頓時一股暖意湧上心頭,打更的宦者面露喜色:「那麼,接下來只等代王登基就成事啦。」
「還早。」秦震搖搖頭,臉上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:「談子,你可有辦法將兵權弄到手?」
「這……」打更的宦者被秦震問倒,支支吾吾回答不出來,原來這宦者叫趙談,與身邊的北宮伯子皆為童侍,因名一字談,秦震為了與北宮伯子作區分,故後加一字子。
所謂的童侍,也就是當他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,就被閹了送入宮中當宦者,趙談與北宮伯子這二人行事倒也機靈,口風又緊,秦震因此將他們收為下屬。
兩人幼時進宮很得人緣,數載後年紀稍長,二人更顯出色,趙談生得白淨清秀;儀態萬芳,北宮伯子亦不遑多讓,秀雅脫俗;風儀端麗,兩人各有特色。
不少宦者看上他們,但無奈二人早被秦震這個油鹽不進的傢伙收為下屬,官職比他低的沒膽子來陰的,官職比他高的倒有不少人,但想使壞的卻一個也沒有,因為那些人都失蹤了,沒人知道是怎麼回事,但大家都猜得出是怎麼回事。
自此,眾宦官只敢遠望趙談、北宮伯子二人而不敢褻玩。
而秦震入宮時也算是個童侍,但他這童侍卻沒閹割。
因為漢初時期的宦者尚未嚴令非閹人不可,故這時服侍皇帝與妃嬪的宦者,有陽具的倒也有不少人,但這些人之中,大部份都在西宮做雜務或為皇帝辦事,至於東宮的宦者,除了少數與妃嬪偷情的沒有被閹外,剩下的便都是閹人。
秦震卻是這些沒有被閹且亦為清白之身的宦者,講白話點,他是一個未與妃嬪偷情的童子身宦官,就憑他那副尊容,隨便一位淫穢的妃嬪想要偷情,寧可找個白淨俊秀的閹人來偷,也不願找他,這句話後來被東宮的人傳出來,劉邦聽了倒是一笑置之。
或許劉邦打心底也同意這番話,若不是秦震生得那肅然模樣,面首之位怕是輪不到籍孺,同樣的,劉邦也不會放心讓他住在長樂宮為呂雉辦事。
「伯子,周勃和陳平那邊有何動靜?」秦震不再理會趙談,向另一人問道。
北宮伯子恭敬答道:「太尉與右丞相那似乎少了內應之人,一直無法打探到呂氏族人的情況。」
「都已潛伏許久卻仍未打通關係,他們那群老臣的壯志只怕也隨著先帝而去。」秦震搖頭嘆氣,往永壽殿的方向望去,久久不語。
趙談與北宮伯子不敢出聲,靜靜等候指示。
三人就這麼站在庭院,一刻鐘後,秦震方才嘆道:「這渾水現在已然談不上是涉或不涉,而是深或淺了。」
秦震返回屋內命兩人磨墨、備蠟泥,他從懷中取出白絹,待墨磨好,便提筆在絹上寫了些字,等字墨乾了,將絲絹反覆對折成半個指甲蓋大小,裹上蠟泥成丸後,將蠟丸交給趙談。
秦震還未來得及吩咐一二,門外就傳來倉促的步伐聲,他起身一看,竟是近年頗受呂雉寵愛的小宮女娥女,其秀麗的容貌染上一抹嫣紅,纖纖玉手撫著微微起伏的胸口,嬌柔的模樣令趙談與北宮伯子兩個閹人都禁不住想對眼前女子使壞,令其成為胯下之臣,可惜這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幻想。
娥女嬌喘連連道:「常侍,太后傳見。」
「嗯。」秦震仍掛著一副死人臉,不冷不熱;他不疾不徐轉身交待:「談子將蠟丸交給劉章,伯子……」秦震說到談子之名時,聲音便壓低下去,語畢,令北宮伯子即刻去辦,叫上趙談跟著自已和娥女同去。
話說趙談與北宮伯子兩人分頭行事,趙談跟在秦震後頭心裡卻不解:「為何會找朱虛侯為內應之人?」
劉章受封朱虛侯,本為劉氏皇族,但呂雉很欣賞劉章,所以將呂祿的女兒嫁給劉章,劉章曾數次頂撞呂雉,但呂雉都原諒他,因而許多劉氏族人很不諒解的將其視為諸呂一派。
至於呂雉對劉章有多欣賞?只要知道呂雉在重病期間,將劉章與其弟濟北王劉興居安排入宮就很清楚了,雖然後世人解讀,這是呂雉要在死前,扣住劉章與劉興居成為人質,令齊王劉襄不得在她死後作亂,但這並非完全正確。
所以這就是趙談的困惑,但現在他沒有時間去想,他只要辦好秦震所交代的事即可。
三人來到永壽殿外,一些官職較高的劉氏皇族都在這,至於殿內則擠滿了呂氏族人,而頗受呂雉欣賞的劉章,卻被呂族人排擠在殿外等候。
秦震刻意走到劉章面前沒幾步,轉身對趙談道:「這沒你的事,回去等候。」眼神卻看向劉章。
劉章查覺到對方的眼神,原以為對方只是眼尾掃到自己,卻不料秦震向自己使了個眼色。
「是。」趙談低頭示禮,這應聲卻刻意喊得嬌聲細語,讓一些原本對趙談就有色心的人爽上心頭。
「永寧殿側。」秦震卻在此時悄聲道。
待秦震入殿後,趙談旋即離去,劉章卻一步也不動站著,彷若沒聽到秦震適才的密約。
朱虛侯劉章在呂雉眼中是個膽大妄為卻心思細膩的武人,既有武勇又有急智,既然要做妄為之事,就要先找到解套之法,不讓自己陷入不必要的危機。
如同數年前,呂雉在某次節日酒宴命劉章監酒,劉章藉機向呂雉要以軍法監酒,呂雉不以為意的答應了,豈料有呂族人逃席,而被劉章以軍令斬了,呂雉表面上非常不悅,心底卻頗佩服劉章,這就是呂雉所欣賞的地方。
宴會結束後,呂雉私底下誇讚:「季(劉邦)之子孫,唯章而已。」這句話的意思是,呂雉只承認劉章是劉邦的子孫,其他人並未擁有像劉邦那樣的帝王氣魄。
話雖如此,但諸呂之人實在是太過愚蠢,他們都以為呂雉這番讚許,只是為了挑撥劉章與劉襄兄弟的感情,令劉氏皇族內鬥,但後世傳紀中,為了將劉呂惡鬥劃分清楚,而未記錄這段話。
由此可知劉章並非魯莽之人,他雖然明知秦震有事找自己,卻不急著離開,直至片刻,才以解手為由赴約而去。
劉章雖然應約而至,但不代表就信任秦震,他悄悄走在黑暗中不發出任何聲音,待觀察永寧殿周圍是否安全無虞後,再慢慢繞往永寧殿側查看。
「咳!」劉章躲在角落看了趙談好一會,確定安全後才走出來咳了一聲。
「朱虛侯。」趙談看是劉章本人,躬身敬禮微笑喊了一聲。
「快說吧,我沒多少時間擔擱。」劉章板著臉,他並非討厭宦者,但像趙談這種男兒身卻似小娘子般的宦者,他十分反感。
趙談也不多說,自懷中取了蠟丸給他,這蠟丸本來也沒什麼味,但置於趙談懷中久了,卻有些許芳香氣息,他眉頭一皺伸手取來,將蠟丸捏碎,拿出白絹來看。
「這是……」初時,劉章仍舊板著臉孔,但愈看到後面臉色愈顯訝異,狠狠嚥下口水。
「小的不知絹中內容。」
「那秦常侍是否有要你傳話?」
「這倒是有。」趙談笑著點點頭:「事可成,事不可強求;不要主動提議擁立齊王,即可避災。」
「……」劉章聽畢,不發一語轉身離開,內心卻異常驚訝:「不可強求,不要主動,可這……豈有讓我不擁立兄長登基之理?」
趙談代傳秦震這番話,令劉章陷入兩難局面,因為趙談口中的齊王,正是劉章之兄劉襄。
原來這齊王劉襄是呂雉的孫子,只是並非親生,呂雉嫁給劉邦時,劉邦已有一子劉肥,劉邦登基後,立為庶長子,因為劉肥之母曹氏非明媒正娶,故為側室,而呂雉所生的漢惠帝劉盈為嫡長子。
劉邦死後,惠帝登基,後因劉肥入朝,惠帝讓上座給他,令呂雉大怒暗中賜予毒酒,惠帝知道後告知大兄劉肥,使劉肥逃過一劫,但入朝容易而脫身艱難,他只好將城陽郡獻給惠帝的姐姐魯元公主,最終得以返回封地。
爾後,劉肥在封地渡過餘生,傳位給長子劉襄,承齊王之位。
惠帝在位時,劉襄倒也安安份份沒動什麼壞腦筋,但惠帝死後,呂雉大削劉氏皇族權力,讓自家呂族奪權,這令劉襄很不滿,但苦於大輸呂雉先手,只得忍氣吞聲時至今日。
朱虛侯劉章為劉肥次子,齊王劉襄之弟,故劉章沒有理由,也找不到理由不擁立兄長。
劉章反覆思考秦震之言,秦震並非不讓自己擁立其兄,反要自己不可主動提議,這豈不是意味著眾臣心中早有其他人選?若以資格來看,能比大兄還要優先順位的,也就只有叔父代王劉恆與淮南王劉長,那麼究竟是那一人?
另一邊的北宮伯子,聽從秦震指示來到長樂宮一處,心頭禁不住亂跳,沒想到常侍竟要他去鐘室。
自從淮陰侯韓信死於此室後,據傳有不少古怪之事發生,例如夜半無人,卻時有嘆息聲或怒吼聲自鐘室裡那頂大鐘傳出,更甚有鐘聲自響;無風自搖,令耳聞者嚇的屁滾尿流,病了數月仍未安好。
爾後,鐘室成了避諱之地,就連白日也不願有人路過。
北宮伯子深深吸了口氣,往那門板敲了一長一短的音,就這麼連敲三次才停下,他忐忑不安地站在門外。
「來者何人?」一道無法辨別是男是女的聲音自北宮伯子耳邊傳來。
「辰時落雨。」趙談回應。
「刀下留人。」
「斗膽一問,您是……」聽到對方說出暗語,北宮伯子總算放下心來,這是人不是鬼,但他轉身探尋卻不見人影。
「莫問,繞到後頭。」北宮伯子點頭,隨即繞到鐘室之後,見到了那人。
這人是個白頭老叟,面有白鬚鬍眼角下垂;腰微彎身體瘦長,雙手抱胸,看似有些猥瑣,但臉上笑容卻不失熱情,一身玄色勁裝,腰掛酒葫蘆。
北宮伯子走到老叟面前正欲開口問話,老叟卻拔了酒葫蘆塞子將葫蘆遞去,北宮伯子嗅到酒香,知道是酒,便取過去痛飲數大口才停。
「會飲酒的是好漢!」老叟比了個大姆指,將葫蘆拿回來喝了幾大口才道:「太尉有事吩咐?」他這時的聲音不再是男女莫辨,而是沙啞蒼老的喉音。
「還需多久?多少人?」
「不好說,至少還需一月餘,人有近千眾。」老叟咂咂嘴。
「足矣,仲秋之際大事將起,東西準備好後會放在鐘室內。」
老叟嗯了一聲,左腳輕輕一蹬就飛至樹頭:「萬事小心,別了,小兄弟。」老叟離去之際似有無盡感慨,竟放聲高歌:「大風起兮雲飛揚,威加海內兮歸故鄉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」
北宮伯子不知為何竟聽得如痴如醉,甚至覺得這老叟在最後語氣聽來竟有些哽咽,令自己無法忘懷這有著神秘魅力的老叟,最後他平撫心境望向老叟離去的方向,內心十分敬佩:「不知常侍怎會和這些人有來往,不對,常侍是用太尉之名,那應該是太尉認識這些人才對,哎,不管了,回去睡悶頭覺吧。」
最終,趙談與北宮伯子二人算是完成秦震的交待。
話說朱虛侯劉章與趙談密會結束後,先是回府一趟交待事項,再返回永壽殿外候著,而秦震進殿後仍未出來,他開始認真思考秦震究竟是何人物?他只知秦震幼時就跟了先帝,但關係應該不及籍孺之流,帝崩後跟了呂雉,但也不如審食其這面首,這秦震真是一個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物。
想來,劉章應是大事將近而無暇思慮,若他能仔細想想籍孺之言,或許能猜得出一二。
說到秦震,他由宮女娥女領進永壽殿,諸呂異樣的眼神紛紛瞧上他,兩人穿過前殿庭走過中庭與重重迴廊,終要抵達呂雉寢室,這時卻有一人當了攔路狗。
「我道是誰,竟是你這宦者。」這攔路人身著曲裾深衣;襟袖鑲上重重花邊顏色亮麗;頭戴大冠,一手指著秦震,那大袖不時搖來晃去,看的都叫人要暈了,他的長相倒也稱得上俊秀,雖然上了年紀更顯穩重,只是現正發著怒氣,絲毫氣質也無。
娥女還未來得及開口,秦震倒是將對方指著自己的手指向一旁撥去:「太后傳見,與左丞相何干?」秦震反客為主領頭走,娥女趕忙跟上。
「太后連本官都未見,你這宦者憑什麼!」左丞相不甘心,再次衝向前去攔了下來。
秦震譏諷道:「審食其,你這左丞相所做之事與吾等宦者又有何差別?」
「你─」審食其怒目咬牙指著他。
秦震冷哼一聲:「滾!」眉宇間所隱藏的殺氣盡顯無遺,左丞相竟是被嚇的一楞,不敢再阻止,只得乖乖目送兩人進去。
「太后,秦常侍求見。」娥女通報一聲後輕啟寢門,待秦震進門後闔上,領著秦震在小廳候著,她則步入廳邊寢房內。
秦震看著寢房傢俱,多以沉香木所制,房中佈置簡單,僅以白紗絹做裝飾,愈顯高貴典雅,而室內出奇地沒有那些華美珠玉與瑰麗晶石,甚至連金玉珍品也未有一件,秦震心道:「呂雉也變了不少啊!」
片刻,內寢傳出一女聲,言語之間可見其語重心長之意:「侄兒啊,切記我所囑咐,否則呂族盡滅,唉,都散了,我還有事交待常侍。」
「是。」有人應聲後一同從太后的寢房走出來,只見這二人,較高者著淺色袍,較矮者著深色袍;領口鑲水雲金邊;大袖滾上雙花邊;頭戴高冠,兩人面容相似,額寛鼻尖;厚唇臉窄,一人有蓄鬍。
兩人出來見到了秦震,倒也沒什麼驚訝,反向他露出笑容微微點頭,原本跟在後面的娥女搶先走到前頭替他們開門。
「太傅、上將軍。」秦震仍舊那副不冷不熱的表情,躬身向二人示禮,兩人虛扶一記就步出寢室。
內寢中的女子嚴正吩咐道:「把門守著,別讓任何人進來。」娥女應聲後,將門關了起來,便守在門邊。
這時寢室餘下三人,守門一人,小廳一人,內寢一人。
娥女不明白,怎麼太后傳常侍謁見,此刻卻不出聲,而常侍的膽識是她前所未見,之前斥退左丞相,現在又不理睬太后,這人怎麼這個樣?
這個局面僵了好一會兒,誰也沒出聲,直到遠方傳來幾不可聞的聲音,秦震才打破僵局:「寅時了。」
「我們幾多年未見過面?」軟語呢喃的語態自內寢傳出,似乎是向人撒嬌一樣,這叫娥女著實受了驚,那怕太后與左丞相獨處時,她也未曾聽過太后用這口氣同丞相說話。
「不記得了。」秦震冷淡的回應。
「自戚姬死了以後就沒見過面吧?」女子仍用嬌柔的語氣詢問。
「嗯。」
「我依稀記得,當初季領你來見我時的光景,你本叫秦威震,威震八方挺威風的,季後賜名為秦震,那也是不錯,當時你幾歲?」
「不記得了。」秦震仍是用漠然的口氣回答。
「我記得很清楚,那時你說你十歲,那模樣倒有幾分可愛。」娥女聽太后這麼說著過往之事,不禁與現在的秦震容貌相比,實在很難想像秦震幼時的樣子有多可愛,她趕緊低下頭舉起有如露玉春蔥般十指輕摀小嘴,拼命忍住不笑出來。
「太后喚常侍來,僅是為了懷舊故事?」秦震這時終是開口叫喚一聲太后之名,但仍顯兩人關係生疏,完全看不出眾人所言秦震為呂雉的心腹。
「唉。」呂雉嘆口氣,中氣略顯不足,聽來特別哀怨。「你依舊不能原諒……我嗎?」
「無所謂原不原諒,諸多事情早已無意義。」秦震仍在小廳答話,未曾移步到內寢,娥女見了心想:「常侍真是向天借了膽呢。」她乍然吐出丁香小舌做了個可愛的鬼臉,轉過身來面對門板,彷若被罰站的小頑童,秦震見狀忍不住發噱,這一笑倒是緩和了僵化的氣氛。
「小丫頭又在作怪了,是吧?」呂雉笑著問,秦震卻沒做聲,片刻後才問:「妳希望我做什麼?」
「你這不是明知故問。」秦震不語,呂雉哀怨道:「保下我呂族,解我心頭掛念。」
「因為妳,我保了多少呂族人;為了妳,我已經當了好多年的瞎子啊。」秦震嘆道。
「若武侯復生,我又何必尋……自尋煩惱。」呂雉這時卻有些動氣,原本是要說何必尋你,但最後又改口,可這略為埋怨的口吻,連娥女都聽得出來,何況是秦震。
「就算樊噲復生,此局亦難解,當年若不是先帝早崩,樊噲早已死得不能再死,終是先帝不忍,未下狠手於妳,可妳卻……」
「難解?你說難解,而不是無解?」呂雉聽出秦震話中蹊蹺而雀喜。
秦震卻潑了她一頭冷水:「呂家就妳這麼個女中豪傑,其他人不及妳一二,妳說這是不是難解?」
「呂祿和呂產雖不及我,但也沒你口中說的那般無能。」呂雉反駁。
呂雉說的呂祿和呂產這兩人是她的侄子,也就是適才見面的上將軍和太傅,兩人先後被封為趙王、梁王,呂雉重病後,為保呂族人安危加封其兩人為上將軍與太傅各掌皇城北、南軍,此二人雖非愚昧,但其下的子孫卻捅了不少婁子,有些都讓秦震暗中處理掉了。
「此二人倒也有些能耐,可惜過於小心謹慎,膽子不夠大,再加上妳這些年的庇蔭,小事有餘,大事不成。」
「呂祿封將統領北軍,呂產領南軍,兩軍盡為我所用,再加以陳平與周勃不合,且陳平向來膽小又傾心於我,政權又豈能有失?」
秦震聽呂雉駁斥後便不再出言。
「這水你能不能別涉。」呂雉深知秦震有多少能耐,最後她還是屈服了,率先開口哀求,只為求得秦震開口保下族人。
「渾水我入得深,已與涉不涉無關。」
「你─」呂雉為之氣結。
「我都這麼求你了,難道你不能看在我過去待你不薄的份上?」呂雉口吻又軟了下來。
「這些年來,有多少事我視若無睹?用盡各種手段殺害劉氏諸王;將戚夫人斬成人彘;以宮女之子立帝,不斷削弱劉氏權力,大封諸呂,令劉呂內鬥,讓朝廷腐敗。」秦震面對呂雉軟語相求,依舊無動於衷。
「你也知道戚姬這事是她咎由自取怪不得我,當年她得寵之際,如何陷我於不義,你不也是知道?」
「所以我舉薦張良為妳擔憂。」
「你可知張良知曉是你推舉他時,他怎麼評你?」
「不知。」
「那你知否,當年你引薦蕭何為我出計謀害韓信時,他怎麼評你?」
「不知。」
「不知不知,你嘴上說不知,那你就不能對此事也當作不知!」呂雉氣急敗壞。
「只要妳能長生不死,政權又何懼推翻。」
「你……除此之外,難道我沒有任何功績或恩典,對於百姓或眾臣?」
「已與適才列舉之事相抵。」
「那你能不能饒了食其?」
「妳嫌他享福享的太短?讓那無能之輩當了左丞相還不夠?就算我饒了他,但天可不留,當年趙姬一事,妳與妳的面首可曾幫過她?」
「我……」呂雉自知理虧,說不出話來。
「這輩子妳的功績無數,皆與生平所做之事全扯平,唯一一件做錯的事,就是不該和審食其媾和。」
「你非得把話說的如此不堪入耳嗎?」呂雉焰氣盡失,只得句句示弱哀求,以期秦震能回心轉意,娥女聽到他們之間的對話嚇的半死,嬌柔的身軀不自主打顫。
「我願意用那龍盤換食其一命。」呂雉仍不死心開口道。
聽見龍盤二字,秦震眉頭皺了一下,眼神若有似無地望向天頂,半晌才冷笑道:「妳所指的無非是龍口觀簷下那頭黃龍?」
「你……你早知曉?」呂雉大驚,她萬萬沒料到最後可以當作交換籌碼的秘密早已被對方知道。
「龍盤是我放的,我如何不知?」
「那你何不取走,儘早離開這是非之地。」
「這妳就不需要知道。」
「罷了,我已將一切安排好,兵權在呂祿和呂產手中,他們只會待在宮裡那都不去,這事動搖不了。」呂雉這下是真的放棄了,雖然她相信自己的安排無錯,但呂族中並無像劉章之流的人物。
直到此時,呂雉才算是真正想通張良與蕭何對秦震的評語,她深深嘆息道:「難怪你曾斷言:『雉死呂滅』。」
秦震冷笑,對於諸呂一輩他向來是看不起的,要不是有呂雉在,他們那有翻身的機會。
「我累了,都出去吧。」呂雉面對秦震事事受挫,她不想也無力再去掌控。
待秦震起身準備離去之際,呂雉輕聲問道:「難道你就如此厭惡我,連進來瞧上我一眼都不願意,你不想看看我是否容顏已老、鬢髮已白、柔弱不堪嗎?」
「容顏未衰,往事卻已矣。」秦震僅留下這句話便離去。
秦震打從入室到離開,未曾進房看過呂雉一眼,這是娥女意想不到的事,她原以為太后在病危之際,所詔見之人必定是心腹,豈料秦震與太后的關係並非如想像中那般。
最終這結果,對秦震與呂雉而言,可以說是不歡而散,這也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。
五日後,呂雉因病而崩。
漢朝並未因呂雉病崩而陷入混亂,反倒開啟大漢盛世。
呂雉死後,呂祿與呂產手握重兵,雖起反叛之心,打算推翻漢朝,卻無膽識去做,因而錯失良機。
仲秋之際,朱虛侯劉章對外令其兄齊王劉襄起兵討伐諸呂,對內聯合太尉周勃、右丞相陳平奪得兵權,最終帶兵入宮將呂氏一族徹底誅滅。
自漢太祖帝崩十五年,歷經漢惠帝、前少帝、後少帝三帝,事事受制於呂雉的諸呂之亂終於畫下句點,漢代將開啟另一個新的盛世光年。
至於誰登基為帝?這已不是江湖人所在意之事。
這朝廷事就讓朝廷大官去煩惱,江湖也有江湖事要解決。
有人說要遠朝廷而入江湖,這天高皇帝遠,江湖事朝廷插手不來,也解決不得。
朝廷爭權奪利,江湖亦要謀權取利,只是這手段不同,結果卻一致。
其實江湖與朝廷沒什麼兩樣,差別只在朝廷人處處受制,江湖人卻是海闊天空。
所謂,位居上朝無所不爭,身處江湖無日不鬥。
江湖有句老話,足以作為最佳詮釋:「我命由己不由天。」
但這可是事實?
故又有云: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」
這江湖事也就從此開始……
2012/9/10完稿,2013/6/17修稿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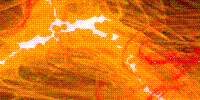
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